2025年4月16日,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“订婚强奸案”作出二审裁定,驳回男方席某某的上诉请求,维持一审以强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的判决。这起案件因其涉及婚约关系中的性同意争议、传统婚俗与法律的冲突,以及司法程序与舆论的互动,成为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法治案例之一。
一、案件核心事实与司法认定
案件始于2023年1月,席某某与被害人通过婚介机构相识,5月1日订立婚约并支付10万元彩礼。次日下午,席某某在婚房内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,导致被害人手臂淤青、窗帘被烧毁,并通过监控录像记录到其将被害人拖拽回房间的行为。尽管席某某辩护称“阴道擦拭物未检出精斑”“处女膜完整”,但法院明确指出,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是“违背妇女意志”,而非性行为的完成度。此外,床单上的混合DNA分型、席某某自述“我既敢做就敢担”的录音,以及其曾书写的悔过书,构成完整的证据链。
法律争议焦点在于,婚约关系是否豁免刑事责任。法院强调,婚姻承诺不代表性同意的预先授权,性自主权始终属于个人独立意志范畴。这一立场彻底否定了“订婚即默示同意性行为”的传统观念,彰显了法律对女性权益的刚性保护。
二、传统婚俗与法律价值的碰撞
案件背后折射出社会对婚约关系的认知分歧。部分舆论曾质疑女方“骗婚”,认为双方已订婚且存在亲密互动,性行为应属“顺理成章”。但法院查明,女方在案发前明确拒绝婚前性行为,案发后及时报警,且已全额退还彩礼,婚介登记信息也显示其无婚姻欺诈史。这印证了法律对事实的严格甄别:情感关系中的亲密程度,不能替代性同意的即时性与明确性。
彩礼纠纷的民事判决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逻辑。法院认定,女方通过婚介机构退还彩礼即完成义务,男方拒收行为不影响法律效力;而订婚宴等日常支出属于情感维系成本,不属于可返还的彩礼范畴。这一裁决既尊重民间习俗,又划清了法律与道德的经济界限。
三、司法程序中的争议与平衡
案件审理过程中,程序合法性成为另一焦点。席某某家属质疑“未出鉴定先批捕”“关键证据仅为电话录音”,但法院指出,程序瑕疵未影响实体证据效力。例如,尽管阴道检测未发现精斑,但床单DNA与其他证据形成互补;而社区矫正调查显示,法院曾拟对席某某适用缓刑,但因家属拒绝配合监管而作罢。这体现了司法在惩罚犯罪与修复社会关系间的权衡。
舆论干预风险在此案中尤为突出。男方家属通过媒体发布“处女膜完整”“未发生实质性关系”等片面信息,引发公众对证据真实性的质疑。对此,法院坚持“证据裁判原则”,通过详细释明DNA检测技术原理、监控录像完整性等专业问题,有效消解了公众误解。这种“以公开促公正”的路径,为类似案件提供了处理范本。
四、案件启示:法治进步与社会观念重构
该案判决具有多重社会意义:
### 性同意规则的明确化
法律重申“无明确同意即视为拒绝”的标准,即便在婚恋关系中,也必须以持续、自愿的沟通为前提。这与《刑法》中强奸罪立法精神一脉相承,打破了“关系亲密可降低同意门槛”的认知误区。
### 司法独立性的彰显
面对“以刑逼婚”等舆论质疑,法院未因婚约背景减轻处罚,也未因民事纠纷影响刑事定性,体现了“刑民分离”的司法原则。二审期间,法院曾尝试通过缓刑修复双方关系,但因男方拒不认罪而维持实刑,更凸显了认罪悔罪在量刑中的关键作用。
### 婚俗改革的催化剂
案件促使公众反思彩礼、婚房加名等习俗的法律风险。法院对彩礼返还范围的严格限定,以及对婚前财产协议的间接鼓励,客观上推动了婚姻关系中的契约意识。
结语
山西订婚强奸案终审落幕,但其引发的讨论远未终止。此案犹如一面棱镜,折射出中国法治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艰难演进。当法律以“违背意志”这一朴素正义观穿透婚约面纱,不仅捍卫了个体权利,更向社会传递明确信号:任何关系都不能成为侵害他人的“免责金牌”。这或许正是该案超越个案的深层价值——在情与法的纠葛中,始终让正义的刻度清晰可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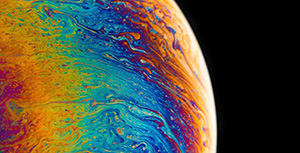

评论区